2025年9月1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全球教席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Sean Cooney以“职业安全卫生与精神健康”为题举办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阎天主持。近百名学生与主讲嘉宾进行了互动讨论,反响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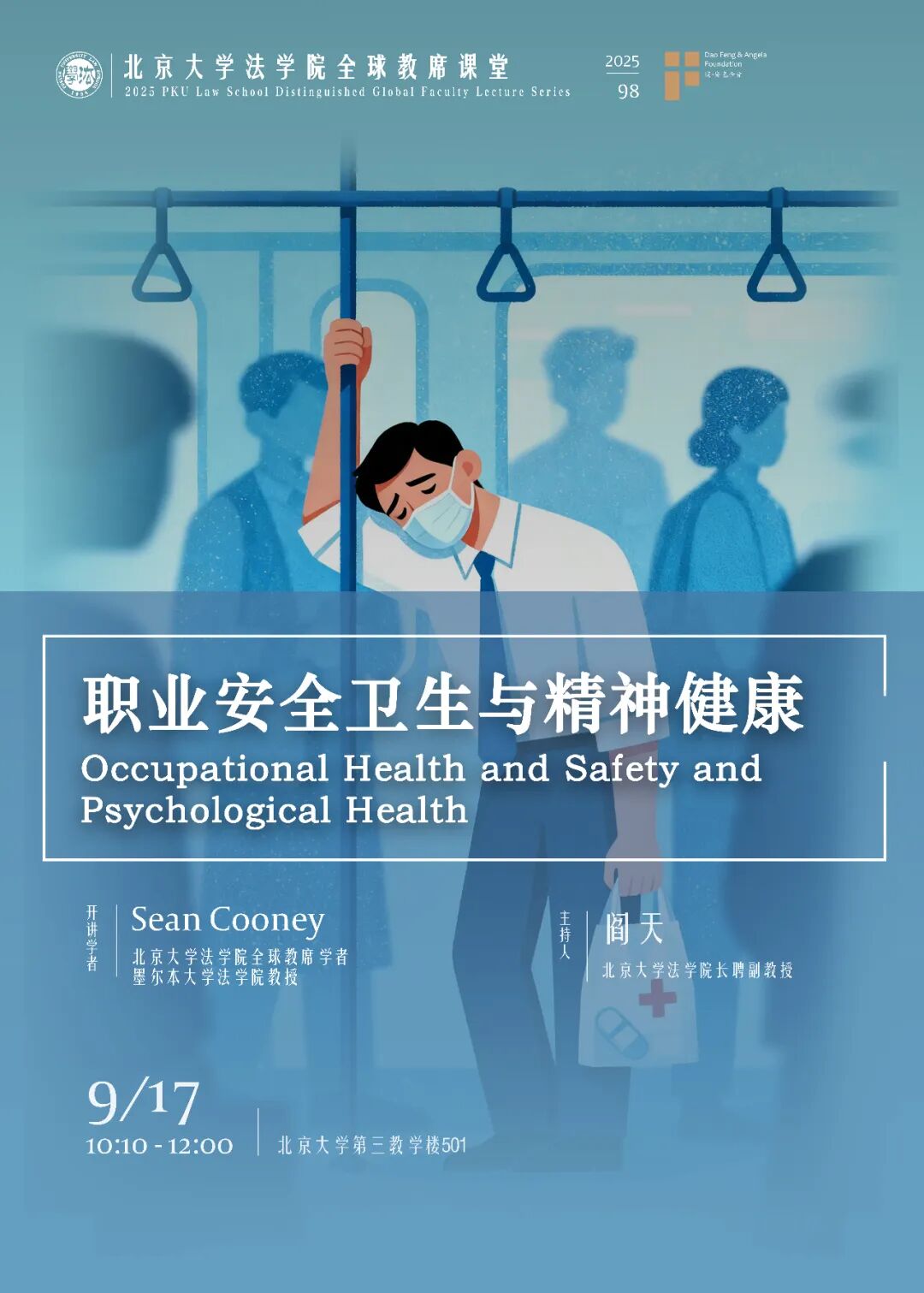
Sean Cooney:
澳大利亚劳动法对劳动者在工作场所面临的 “社会心理危害” 提供制度性保护。根据澳大利亚《工作健康与安全法》及配套条例,“社会心理危害”指源自工作管理模式、作业环境、生产设备或职场互动行为而导致的“心理伤害”。其中“心理伤害”涵盖焦虑症、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病理状态。在现代职场环境下,劳动者不再面临高风险的身体伤害问题,但不良工作关系、职场暴力与骚扰、不合理工作要求等现象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会对劳动者身心健康构成系统性威胁,因此澳大利亚法律将其纳入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体系。
由于《工作健康与安全法》并未采取传统的“雇主—雇员”框架,其保护范围具有广泛适用性:既涵盖标准劳动关系中的雇员,也可延伸至劳务关系当事人乃至于平台从业者。对于用人主体的界定,该法采取了“从事商业或事业者”标准,因此个人经营者、公司、事业单位等均可被纳入该法的规制范畴。《工作健康与安全法》要求上述用人主体在合理可行范围内,保障所聘劳动者及受影响人员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同时,该法构建了完整的用人责任体系与劳动者参与机制:其一,用人主体需遵循“合理可行”原则,即结合风险发生概率、伤害严重程度、行业专业知识及防控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并实施风险消除或最小化措施;其二,建立劳动者参与机制,鉴于外部监管资源有限,法律规定用人主体需与劳动者选举产生的职业健康与安全代表协商,且职业健康与安全代表在面临紧急危险时享有停工权。
在《工作健康与安全法》基础上,澳大利亚《公平工作法》针对职场压力做出补充规定,主要体现在灵活工作安排、“离线权”保障及集体谈判机制三方面。其一,灵活工作申请制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如孕期、育儿父母、残障人士、老龄劳动者等)可申请调整工作安排,用人主体仅在具备合理商业理由并完成善意协商后可予以拒绝。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劳动者“工作—生活”平衡。澳大利亚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职场弹性协议普及率持续提升,印证了制度实践的有效性。其二,“离线权”制度的法律确认。法律明确劳动者有权拒绝在工作时间外响应雇主或第三方的工作联络,除非拒绝行为被认定为“不合理”。判断标准包括联络目的、干扰程度、补偿机制及劳动者个人状况等。该制度的推行为数字时代遏制“加班文化”划定法律边界。其三,集体谈判的风险缓冲功能。以墨尔本大学2024年集体合同为例,集体合同对学术岗位的工作时长、负荷分配设定证据化标准,明确禁止“不合理超额工作”,体现了集体协商机制对社会心理风险的具象防控作用。
提问环节
提问一:澳大利亚《工作健康与安全法》在具体实践中的执行效果如何?有哪些执法手段?
回答:《工作健康与安全法》在澳大利亚劳动法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存在多种执法手段。首先,违反法定义务的雇主可能面临劳动监察部门的干预,具体包括罚款、责令整改以及违法信息社会公示等措施。其次,在企业内部,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代表有权要求停工,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提问二:离线权规则下,劳动者有权拒绝在工作时间外回应雇主联络,除非拒绝行为被认定为“不合理”。那么如何判断这种“不合理”?
回答:关于劳动者拒绝回应的合理性判定,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已有丰富的判例积累。因此,在界定离线权及劳动者拒绝回应的合理性时,需参考既有判例的裁判思路。值得注意的是,离线权在澳大利亚的有效推行并非仅依赖法律的作用,还涉及社会规范与经济因素的协同。澳大利亚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实现 “工作—生活”平衡提供了现实条件。
提问三:当劳动者因社会心理危害向用人单位索赔时,标准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与零工工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回答:由于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制,各州自行制定赔偿制度,导致州间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州将零工劳动者纳入赔偿体系,而另一些州则未作规定。
提问四:法律试图保护心理健康是否也会造成另一种不良的职场文化?法律为职场言论设定了各类禁止性规范,职员虽可避免侮辱性言行,但也需谨慎发表言论。若法律标准持续提高,是否会反而导致职场环境更趋压抑?
回答: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尤其是职场言论的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目前已有不少观点反对“过度风险规避”的倾向。因此,更优的解决方案或许并非依赖法律的硬性规定,而是通过开诚布公的协商机制,在权益保护与职场氛围之间寻求平衡。
